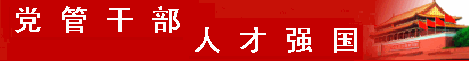选举改革十年破土
中国改革杂志
作者:韩雪
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十年尚难算得上转眼一瞬,但对于投身基层选举制度改革的这些政治精英来说,人生画卷已因为这十年的描绘而截然不同,对于中国选举改革来说,刚刚走过的三千多个日日夜夜为民主政治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学者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发展党内民主,这点已成共识。而党内民主的突破口就在于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公推”意为公开推荐候选人,“选举”则是公开竞选,包括间接的公选和直接的直选。这其中公推直选的竞争性和民主性要远远强于公推公选。从公推公选到公推直选是中国选举制度的一次重大发展,是向民主选举的又一次推进。
公推公选,基层民主的突破点
郭沫若曾说过,“水性”的川人拥有“丰富的革命性、彻底的建设性”。回溯中国基层的公推公选改革,就一定要从四川开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蜀地的达县、南充地区,按照党的十三大关于引入竞争机制、发展基层民主的精神,在部分乡镇进行了公开竞聘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副乡镇长的试点工作。
1997年,党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乡镇选举改革就成为了重要途径。次年,已经试行十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面临修改和正式颁布,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对村民自治的总结与反思浪潮,其中氛围最热烈的就包括四川。而在其他省份刚掀起村委会主任“海选”时,四川巴中已开始直选村支书了。
1998年3月,四川省委在巴中地区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直选村干部经验的同时,鼓励将公推公选扩大运用到选拔乡镇领导干部上。随后在6月的成都会议上,四川省委更对改革乡镇领导干部选任制度进行了部署。而这些,正为改革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挥空间,从宝石镇到步云乡,四川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名副其实的突破点。
1998年的最后一天,在四川步云的细雨中,6236名乡民手中的选票和“中国第一个直选乡长”的突破性改革,将这个偏远的小乡带进了国人的视野。这传奇性的一刻,在推动者张锦明看来却是“顺其自然”。
就在那年年初,雅安市市中区下辖的四个乡镇领导班子多名成员相继出现经济问题,情况最严重的宝石镇只剩下一个镇党委副书记能够正常主持工作,乡民对由传统方式产生的乡镇干部的认可度正在下降。时任区委书记的张锦明急需在短时间内任命多名得力干部,组织基层党组织工作,挽回声誉。对于刚调任不久的张锦明来说,短时间内人选难定。与此同时,大家都有一个考虑,区里任命若再次出事,责任谁担?
随后的区委常委会上,张锦明主张改变原有选任方法,在宝石镇实行“公推公选”,“如果大家来公选,风险至少可以分担。”这个朴素又不乏政治实用主义的初衷,成为宝石镇公选的源头,更直接实践了当时四川省政府关于“扩大基层民主”的思路。
4月,宝石镇进行了镇长公选。在68名报名干部中,通过笔试录取6名。在随后的答辩中,由人大代表、各村干部、村民代表投票产生2名正式候选人,再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投票产生最终人选。宝石镇年仅28岁的区委组织员向道全,成了中国第一个公选镇长。宝石镇镇长候选人还限制在党内提名,而横山镇放开了“仅在党内提名”的限制,结果由非中共党员的邓少斌胜出,成为党外镇长。东禅和莲花两镇,实现了对党委书记的党内公选。
五个月后,四川公布了《乡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推荐乡镇的某些领导职位人选时,还可以采取组织推荐、群众推荐、个人自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而张锦明关于宝石镇“公推公选”经验的介绍,更得到省里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和鼓励。这种政策和领导的“双支持”,对改革的大面积铺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想而知接下来四川基层官员力推的乡镇选举改革热潮。
1998年剩余的几个月时间里,乡镇“公推公选”在四川掀起高潮,形成了遂宁市的“混合投票”公选、巴中与南充市的“量化淘汰”公选、绵阳市的“代表直接投票选举”等多种模式。
四川并非独特,在其大面积试验的同时,全国其他地方也有少量且分散的试点。1999年初,深圳大鹏镇即在换届中试行了“两推一选”。在河南新蔡、福建莆田与龙岩等地,基层选举改革也在进行。
有了“公推公选”镇长的基础,步云乡的“公推直选”从改革的深入角度看来就成了自然,并将四川基层选举改革推上了沸点。然而随之而来的争议以及叫停,是张锦明没有预料到的。
1999年1月19日,刊登在《法制日报》上的《民主不能超越法律》,明确指出直选乡长违法。因为按照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乡镇长应该由乡镇人大代表来选举,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长的直选可能会弱化乡镇人大的权力。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步云并非“直选”之首。在“步云直选”前的1998年5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就已经在眉山市青神县的南城乡进行过一次秘密的乡长直选试点工作。只不过这一尝试在几年后才解密,也正是因为有南城乡直选在先,主推“步云直选”的张锦明才能在争议之中被省委“保全”,调任遂宁市副市长。
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步云乡直选明确表示“不予支持”。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的全国人大“关于作好乡镇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其中明文规定各地换届中,不得对乡镇长进行直接选举。这个被大多数地方政府理解为反对试验的文件,使得选举改革走到了叉路口。深圳大鹏镇等地在接下来的换届中回归了历史途径,但四川的选举改革在省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得以继续发展。虽然这个文件没有抑制四川选举改革的数量,但却直接影响了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更使得这些积极探索的“改革者”演变为体制内的“变革人”。
最直接的体现是2001年,时任遂宁副市长的张锦明主动要求将步云列为自己的联系乡镇。步云的换届选举也变为,由全体选民投票推选出一名乡长候选人,再由党委提名进入人代会等额选举。这次保留直选内核的公选,规避了第一次触及的政治风险,在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中拔得头筹,从体制到民间都获得了最大的肯定。
2001年9月,四川省委组织部下文要求除少数民族地区,至少1/3的乡镇在当年换届选举中要采取“公选”方式。同时还有一个导向性规定,明确要求不再进行乡镇长直选,而鼓励探索乡镇党委书记的直选工作。有了省委组织部的文件作依据,在当年的乡镇换届中,四川雅安市委、南充市南部县委、巴中市委、遂宁市中区区委均颁布了指导换届选举工作的专门文件,中心意思基本是,在县委组织部门确定一个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之前,必须进行一道对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公开选拔的过程。候选人预备人选通过公开报名产生。
在省组织部文件出台后的选举改革中,雅安成了亮点。
雅安乡镇一级公推公选改革的主要决策和推动者是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0年8月调任雅安的魏宏。虽然其在2002年8月,调回省委组织部主持工作,但与此同时张锦明正式调往雅安,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在换届前,雅安市委即颁布了专门文件指导换届选举工作,并决定采取“零起点”竞争的办法,普通干部也可以参加乡镇正职的选举,极大地增强了竞争性。雅安下辖的雨城区、荥经县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随后选举扩展到权力体系中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甚至在妇联亦得推行。
到2002年初,四川除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外,全省40%的乡镇实施了竞争性选举,雅安、巴中等地更达到100%。“公推公选”出了5447名乡镇领导,其中包括787名乡镇党委书记和942名乡镇长。其中,雅安、巴中、泸州等地所有的乡镇党委书记均是通过公推公选产生。同年6月,德阳市中江县又以公选方式产生了县长人选,在全国首开公选产生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人选的先河。
在这场选举改革中,江苏虽后发,却以其迅猛之势、空前之力在改革历程中,留下浓厚的一笔。而这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就是2002年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
江苏省的公推公选改革始于宿迁市。2003年4月到2004年4月,江苏省相继出现了“公推竞选”党政正职、“公推差选”乡镇长、“差额直选”和“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等模式。此后,在江苏省委的组织下,淮安的清河、淮阴,金坛和沛县,公推公选在江苏省境内由公开竞选乡镇干部到公推公选省管干部、由县处级递进至副厅级、由中小城市推进至中心城市,大力推进、迅猛发展,掀起了新一轮选举制度改革试点。
公推直选,党内民主的系列试点
早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就要求加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并制定了以“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目标。作为落实工作,1995年2月,中央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首次规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步骤与程序。
2000年6月,党中央又总结了十三大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就和经验,制定了《2001——20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党政干部制度改革,重点是深化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按照这一重点要求,2002年7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规定了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六项基本程序,即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职、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为干部选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规范。
同时纲要也提出,“积极探索在差额选举的条件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充分发扬民主的方式方法。”至今,各地仍在针对这一改革重点与难点,积极探索和推进。事实上,选任制干部改革的难度和风险比委任制干部改革要大得多,推进过程中难以预料的问题随时都会出现。然而在这条改革道路上,中央的指导和地方的探索都从未停滞过。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操作空间。
从全国范围内的基层民主改革实践来看,试图进行乡镇长公推直选改革的地方都需要尽量避免触及现有法律规定和政治体制框架的问题。乡镇长直选涉及全体选民,程序复杂,难以组织和控制。相对来说,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因只涉及到党员和部分群众,实施直选的操作更为实际。由湖北、江苏、四川等省带动的一系列试点,使基层民主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基层乡镇党委内的公推直选。
2002年,湖北省在全省乡镇党委换届中,确定了11个乡镇进行“两推一选”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试点工作。9月,京山县杨集镇在全国范围内最早进行了乡镇党委书记直选。
2003年2月,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实行“两票推选”。所谓“两票”推选就是乡镇领导干部在产生过程中,必须首先获得群众的推荐票,并按照群众推荐票的多少决定进入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候选人资格,然后再接受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选举票。在总结和改进咸安模式的基础上,在全省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和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书记镇长一肩挑。随后的2004年,襄樊市将“公推公选”的职级扩大到了县(区)级,公选产生了樊城区区长和老河口市市长,襄樊成为湖北省第一个公推公选市(县)区行政一把手推荐人选工作的试点。次年年初,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在湖北全省范围内全部推开。
第二个进行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的是四川成都的新都区。新都改革的模式简言之就是“一二三四”理论:打造“一个阳光政府”;开放“两个会议”——区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推进三个层次的直选——教育系统内全面推行“校长直选”、开展镇党委书记直选试点、完成全区所有299个村党支部书记的直选;进行四个层面的“民评官”——评议区级党政领导、评议区级各部门领导、评议镇级领导、评议村级领导。2003年年末,新都区木兰镇举行了第一次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此模式随后在新都全区、乃至成都市推开。
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平昌的试验显然是扩大党内民主的典型。平昌县9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时,125名外出务工党员中116名回乡参加了选举。在预选中,平昌规定不但全体党员可以参加,还吸收群众参与,共有726名群众参加了推荐会进行投票。事实上,民主已经从党内扩及党外。
直选基层党委书记的选举改革,在2005年8月得到了四川省委的认可和大力推广,组织部下发文件在全省普遍推开乡镇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
2004年4月,党内的基层民主改革开始了由局部改革、单项突破的“试验点”向全面铺开、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的转变。中共中央颁布《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文件,加上此前经中央同意、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合称“5+1”文件,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成果和实践经验,及时的用制度巩固下来。
2004年7月的重庆渝北区、8月的云南红河州、2005年5月的陕西南郑县湘水镇,“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的党内基层民主改革,已呈现遍地开花之势。
2004年11月,江苏省对拟任无锡市委书记的人选以无记名方式进行了全委会票决。开启全委会对县市区党政正职进行无记名票决的先河。
隶属于江苏宿迁的泗洪县,是江苏省最早的公推直选县区级试点,更是我国首个全县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的改革试点。2005年7月的泗洪直选,全县1万多名农村党员都直接参与了选举镇党委书记的过程。这场党内基层的民主试验,成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进程中的一大突破。
2006年3月,江苏仪征的10个乡镇也成为一场党内政治制度改革的试点。在省内首次实现,由乡镇全体党员通过公推公选的形式,直接选举出乡镇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党委班子成员。
基层和地方的试点经验与创造成果也得到了中央的尊重和肯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要求“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在2006-2007年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中,几乎每个省份都进行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试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更进一步总结党内选举试点改革的经验,明确提出“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更将体现“平昌直选”经验的“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明确出来,肯定了非党员群众具有参与推荐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候选人的权利。在基层选举制度改革上,已将民主的扩展趋势,从党内向党外表露无疑。
这些地方自主的、以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政治民主为内容的选举制度改革实践,无疑扩大了在基层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民主成分。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性、参与者范围的扩大性,增强了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推进了选举制度的民主化进程,把群众路线和群众公认原则切实贯彻到干部人事改革工作的各个方面,更成为实现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一步。
在村民自治、村委会直选的基础上,中国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直选正在逐步推进。十年的时间让这场基层选举制度改革的参与者或关注者都清楚地看到一点,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一个渐进的、增量曲线,是一个从外围或边缘地带向核心逐步推进的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循序渐进的耐心、扎实推进的毅力,以及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向往。